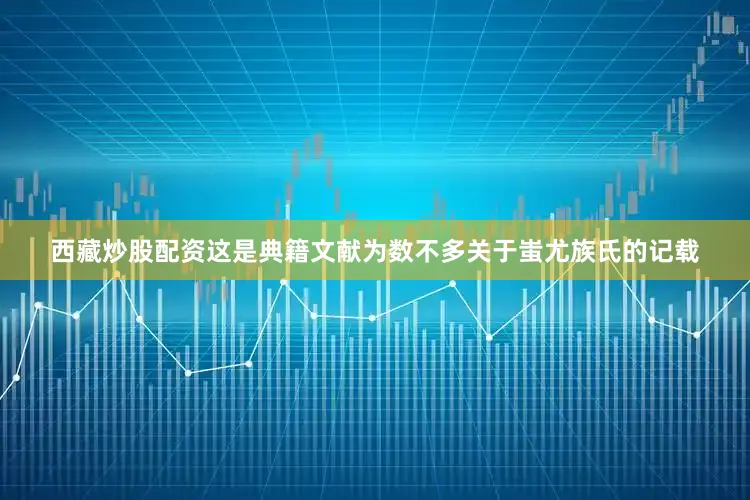武汉,作为武昌、汉口和汉阳三镇的统称,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发展轨迹。到了民国十六年(1927年),三镇正式合并,成立了京兆区,之后才正式定名为“武汉”,成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城市。
1938年10月25日,经过长达数月的激烈战斗,武汉会战宣告结束,武汉彻底沦陷,落入了日军的铁蹄下。对于武汉的三镇百姓来说,这标志着一段近七年惨无人道的生活的开始,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,才结束了这段噩梦般的岁月。
从楼上俯瞰武汉的街道,日军的军车一排排地停在路边,四周的街道显得冷清而荒凉。画面左侧可见一座叫做“北支烟公司”的建筑,而右侧则是另一座标志性的“十合公司”。这一刻的武汉街头,行人几乎没有,取而代之的是日军士兵的身影,几乎所有活动都由他们主导。
展开剩余85%武汉街头的建筑风格混合了中西方的元素,大多数是民国初年时期建成的。街道两旁并排着几家大药铺,其门前高悬着醒目的招牌,一家是“傅济春参燕国药号”,另一家则是“长寿参燕国药号”。这些药铺见证了那段历史的风云变幻,街道本身也透露着那个时代的气息。
江汉路,位于汉口的核心区域,是武汉的商业中心之一,被誉为“二十世纪建筑博物馆”。图中的牌楼,曾由日伪汉奸在江汉路上竖立,意图庆祝武汉的沦陷。这座牌楼成为了那个时代悲剧的见证,也是日军及其支持者极力推销“胜利”的象征。
日本侵占武汉期间,日本妇女几乎是随军而来,哪里有日军,她们的身影就出现在何处。这张照片中,一群身穿和服的日本女性,头戴灯笼,手持膏药旗,集结在武汉街头。她们身着的衣物上缀有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的字样,显得非常庄重,准备参与“胜利”游行,来庆祝他们的所谓“战果”。
为了讨好日本人,一些当地的汉奸们组织民间艺人进行街头表演。这张图片中,两名男子正在高跷上表演叠罗汉,周围围满了市民观看。尽管有许多围观的百姓,但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更多的是无奈和沉默,而不是欢愉和支持。
江汉关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建于1927年。它由主体建筑和顶部的钟楼组成,是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。日军占领武汉后,江汉关被改作日本汉口碇泊场司令部所在地,专门负责日本陆军的水上运输工作。对于武汉人来说,这个曾经辉煌的建筑如今充满了敌军的气息。
远处的黄鹤楼旧址,那座曾经辉煌的建筑在1884年遭遇一场火灾后彻底毁坏。直到1933年,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一些小亭台楼阁,西向东地依次排列着警钟楼、奥略楼和抱膝亭等。照片中的抱膝亭便是其中的一部分,它是湖北学界为纪念晚清学者梁鼎芬而建,前面立着黄兴的雕像,成为这片区域的文化象征。
在黄鹤楼旧址旁,有一座被称为“孔明灯”或“胜像宝塔”的装饰物,这原本是黄鹤楼前的一处标志性装饰。如今,塔下已是破败不堪,周围摆放着小贩的西洋镜木箱,偶尔可以看到日本士兵的身影徘徊其中。
武汉中山公园的前身为刘歆生的私家园林,始建于1910年。1927年收归国有,之后更名为汉口第一公园,至1929年,正式定名为汉口中山公园。公园内有着众多的木桥和凉亭,景色宜人,却也在战争中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
张公亭是为纪念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鄂业绩而建的。这座纪念亭的历史已有九十年,它静静地矗立在武汉市,是武汉市为数不多的纪念张之洞的建筑之一,也成为了这一段历史的见证。
武汉大学,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摇篮之一,源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。1928年,它被正式命名为国立武汉大学,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,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历史与变迁。
在武汉郊区,有一座单拱石桥,虽然桥面已经破损严重,但坚固的桥体依然屹立不倒。这座桥见证了历史的沉浮,也透露着战争过后武汉的不易。
随着日军侵占武汉,交通要道上的碉堡变得密布。这座巨大的碉堡位于武昌城外,坚固的结构让它成为日军防御的关键点。周围的民居早已被拆除,只有这座碉堡坚守在那里,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个关于占领与抗争的故事。
碉堡附近,伪军站岗守卫,手持长枪。照片中的伪军身材较为矮小,装备简陋,手中的武器显得格外沉重。拍摄角度的巧妙让这张照片中的伪军显得有些不协调,但他们的身影仍然令人感到压迫与悲凉。
山坡车站,位于今武汉市江夏区,建于1917年,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。照片中的站台上,几名日本兵站在站牌下,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和压抑的气氛,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无情战局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门户首页地址,如何开户炒股买股票怎么开户,配资炒股平台找加杠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正规配资开户没收违法所得20.22元
- 下一篇:没有了